对暴风雨、打雷、闪电的描写
岁时杂编
…
猛地电光一闪,照得屋角里都雪亮。幔外边的巨人一下子把那灰色的幔扯得粉碎了!轰隆隆,轰隆隆!他胜利地叫着。呼——呼——挡在幔外边整整两天的风开足了超高速度扑来了!蝉儿禁声,苍蝇逃走,蚊子躲起来,人身上像剥落了一层壳那么爽。霍!霍!霍!巨人的刀光在长空飞舞。轰隆隆、轰隆隆,再急些,再响些罢!
——茅盾《雷雨前》
——王蒙《雨》
——[日]德富芦花《自然之声》
夜雨款款地剥夺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像又格外敏感和畏怯。这种畏怯又与某种安全感伴和在一起,凝聚成对小天地中一脉温情的自享和企盼。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贴;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籍。
暴雨和雷雨是多么欢势,它们驱走暑热,它们解除干渴,它们弥合龟裂,它们叮叮咚咚地敲响沉闷的大地,它们咋咋唬唬地嬉闹着对人们说:“别怕,我们折腾一会儿就走。”
似水晶、非琉璃、又非玻璃,霎时间了无形迹。
为什么这几年在北京很少见到大雨冒泡儿了呢?是气候变了么?是我事太多、心太杂,对似水晶又非玻璃的泡儿视而不见,这泡儿已经唤不起我童年的那种好奇的沉醉了么?呵!
像有一只巨人的手拿着明晃晃的大刀在外边想挑破那灰色的幔,像是这巨人已在咆哮发怒;越来越紧了,一闪一闪满天空瞥过那大刀的光亮,轰隆隆,幔外边传来了巨人的愤怒的吼声!
坐了片刻,乌帽子岳上空,浓云翻卷,色如泼墨。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殷殷雷鸣。顿时,空气沉滞,满目山色变得忧戚而昏暗。忽然,一阵冷风,飒然拂面。湖水声,雨声,摇撼千山万谷的树木枝条的声音,在山谷里骤然而起,弥漫天地。山岳同风雨激战,矢石交飞,杀声震耳。
这一天上午,天空老张着那灰色的幔,没有一点点漏洞,也没有动一动。忽然天空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条缝!不折不扣一条缝!像明晃晃的刀口在这幔上划过。然而划过了,幔又合拢,跟没有划过的时候一样,透不进一丝儿风。一会儿,长空一闪,又是那灰色的幔裂了一次缝。
抬眼远望,乌帽子岳以西诸山,云雾蒙蒙,一片灰蓝。这里正当风刀雨剑,激战方酣之时,国境边上的群山,雪光鲜亮,倚天蹈地,岿然矗立。中军、殿军排列二十余里,仿佛等待着风雨的袭击。宛如滑铁卢的英军布阵,沉郁悲壮。使人感到,处处浸满大自然的雄奇的威力。大壑上面,突现者一棵古老的橡树,一只枭鸟兀立枝头,频频鸣叫。雷声大作。云在我的头上黑黑地遮蔽着。风飒飒震撼着山壑。豆大的雨滴,一点——两点——千万点,噼噼啪啪地落下来。
小时候,我最喜欢北京城夏日的大雨。雨中,积水上冒出一个又一个的半圆形的小泡儿。
在夜雨中想像最好是对窗而立。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热气呵成一片迷雾。你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却似乎又能看得很远。风不大,轻轻一阵立即转换成淅沥雨声,转换成河中更密的涟漪,转换成路上更稠的泥泞。此时此刻,天地间再也没有什么会干扰这放任自由的风声雨声。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雾气,看见了窗子外层无数晶莹的滴雨。新的雾气又蒙上来了,你还是用手指去划,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让大雷雨冲洗出个干净清凉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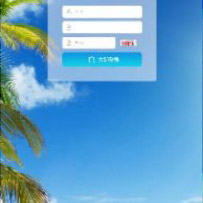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