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岗茶香
…
“眼下再艰苦,也比旧社会强万倍!”
一踏上长冲岗,看到那一片连绵起伏的茶山,感到又熟悉又生疏,又亲切又可爱。山坡上新翻过的梯地里,齐腰深的茶蓬,在灿烂的阳光下,油然地闪着点点绿光,就象墨绿墨绿的龙,一条一条地弯弯曲曲地盘卧着。茶龙间,一排排的黄花菜苗,嫩绿青翠,把整个茶山点缀得一派春意。还有那砌在梯地上的道道石岸,一层高一层,直递蓝天。仿佛在向人们显示着茶山主人“欲与天公试比高”的雄心壮志。
茶叶,很早就是英山的一大特产。但是过去,人们只是在山边地角种上几棵茶,用“一刀切”的方法采下来,手工制成粗糙的黄大茶,我在英山工作时喝过不少。到了大跃进年代,英山县的茶叶生产才有很大的发展,不少象长冲岗这样乱石成堆、寸草不生的荒山秃岭变成了丰美的茶园。近几年,根据国家出口和内销的需要,他们又改制绿茶了。想到这里,我连声赞道:“好!要是不晓得长冲茶场历史的话,真想不到这样好的绿茶的产地从前竟是一个荒岗。”
“怎么不在,他现在是我们茶场的负责人,还当上了县委委员呢。走,我引你去找他。”
人们都是这样,对于自己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总有一股特别亲切的感情。事情也凑巧,这次我们到英山县写作实践,而我又恰恰被分配去长冲茶场,这真是十载难逢的好机会。我怀着急切的心情,朝长冲茶场奔去。
怎么忘得了啊!那大跃进的日日夜夜,那千军万马大战长冲岗的热闹场面……
老李正在东边山头上垒石岸。当我们走近时,只见他正抱着一块山羊一般的大石头往上砌,额上不时地掉下几粒汗珠。
我凭着记忆,快步地向十年前住过的茅棚所在地走去。
和煦的阳光,洒满了苍峰茶海。这时,饭后开工的人们,扛着钢钎、铁锤、锄头,挑着箢箕,唱着歌儿,象出征的战士,英姿焕发。
茶场的五口水塘都露了底,天还是不下雨。
“这呀,”王大伯笑着说,“还不是象洪成说的,也是靠斗出来的。”
“修这么长的渠道,真不简单哪!”我赞叹着。”
一九五九年冬,公社党委响应毛主席关于“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的号召,组织了治山建场队,由党委副书记李洪成带领,开进了长冲岗。我随区工作组的同志,也参加了这场战斗。
“哈哈,场部和职工宿舍都早搬到山那边去了,这已经是我们茶场的小学啦!”王大伯笑着,笑得是那么自豪。
春英已经把茶泡好了。那茶汤色明亮,香气扑鼻,喝一口后,嘴里久久留下一股甘香的味道,给人一种轻松舒服的感觉。王大伯看我喝得律津有味,问道:“这绿茶的味道怎样?”
王大伯认真地说:“变化实在是大,全靠毛主席指路。”他醉心地望望眼前碧绿的茶海,“茶园建成这个样子,是靠斗出来的。老徐,当初我们在老李带领下大战长冲岗的情景,你兴许还记得吧?”
刚到。”我指着山下说:“正想到这里来找场部呢。”
“洪成,你看谁来啦。”王大伯不等我开口,就大声叫嚷着。老李回过头来,看见了我,立刻放下石头,跑上一步,照老规矩扎实实地捅了我一拳:“哎呀今天刮的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哪里还有茅棚的影子!只见两排整整齐齐的瓦房,中间夹着一块操场,一大群孩子,系着鲜红的领巾,有的在打球,有的在唱歌,有的在调皮地互相追逐着。操场边的杨柳吐着嫩绿的枝芽,房前的几株桃花迎着灿烂的阳光竟相开放。
路旁,一条石砌的渠,缓悠悠地流着清水。渠边一蔸蔸剑麻伸开着一把把剑样的深绿色的叶子。整个水渠,宛如一根镶了绿边的银白色的带子,在茶峰间穿来绕去,时隐时现。
“那阵子,老李是够担风险的。记得有一次,那个一心想砍掉茶场的“上级来到这里,见茶场不但没有下马,反而扩大了几十亩,便指着老李的鼻子直嚷:“你违反上级指示,我要撤你的职!”他以为这么气势汹汹就可以把人吓倒,没想到听了老李一席话,他气得两手发抖,划火柴想点根烟都点不着啦。”春英几句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原来,在一九六六年,茶场遇上了一场特大的干旱。刚采过春茶,天就旱起来了,一连四个月没有下雨,太阳象一团火球,地象一块烙铁,茶树都旱得快卷了叶。为了救茶树,全场男女老少都出动了,用桶把水挑上几十米、百把米高的山岗,昼夜不停。可是,人们不知流了多少汗,挑来一担水,只能浇两棵茶,水往地上一倒,“嗤一”地冒着白泡,过会儿一看,地照样张开于裂的嘴,茶树还是没精打采的。
“担任这项工程的总指挥,就是我们华刚大叔呀。”老李拍着王大伯的肩膀边走边说。
离开长冲茶场已经整整十年了。
“倒不是什么风吹来的,而是茶场这朵花越开越艳,把我给吸引过来啦。”我一边笑着说,一边打量他,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敞开着,肩上打着补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是那么精神,精力还是那么充沛,只是挂着汗珠的额上添了几道皱纹,冒着热气的头上多了几根白发。我禁不住说:“你还是不减当年勇啊!”
这几句话是多么深刻啊!的确,哪一棵树的成长不经历风风雨雨?哪一条船的航行不碰到风颠浪击?革命事业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长冲茶场所走过的道路,不正说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可不,在这荒岗上兴茶,不是一帆风顺的。你离开那年,刘少奇一伙鼓吹三自一包的妖风刮到这里来了,逼着要茶场下马,一小撮阶级敌人也遥相呼应,煽风点火,要茶场退山退地,有的还扬言要上山挖我们的茶苗。”老李呷了口茶,不急不慢,余愤未消地说。
是啊,一切都变了!昔日的长冲岗,遍地麻骨石,大大小小六十几个山头,全是和尚的脑袋,光秃秃的,寸草不生。然而,眼前展现的却又是一幅多么美丽壮观的画面啊!
“这是什么时候修的?”我指着水渠问。
山腰间,青年们挑土抬石,来来往往,快步如飞;山脚下,妇女们正在挥锄松土;山背后,传来开山凿石的阵阵锤声。我被这热闹的劳动场面和大上快上的磅礴气势所吸引,立刻脱下棉袄,和老李他们一道干了起来。
他自豪地拍了一下自己宽阔的胸膛,笑着说:“还不错,看样子还能干一二十年啦!”
以后,因工作需要,我被调离了长冲茶场。
“你还认得她吗?”王大伯问我。
要战胜干旱,首先要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老李抽空到县城买回几本《大寨精神大寨人》的小册子,领着支委们认真学了起来。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大寨贫下中农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大大激发了茶场干部和广大职工的革命精神。整个茶场沸腾起来了。一百多个职工齐上阵,苦成了七天七夜,修了一条十华里长的渠道,接通了松山铺水库的总干渠,引来了水,救活了茶树。
老李说:“嗨,现在你就是打她骂她,她也不哭了。去年她被选为场党委委员,当了科技组长,不仅学会了育茶、制茶的技术,还到过好几个县里介绍种茶经验呢。”
“怎么不认得,我还记得她常哭鼻子呢!”我说得大家都笑了。
他俩几乎同时答道:“文化大革命中。”
是的,经过几百双手苦战了半年多的时间,终于开出了近两千亩茶园,让荒山第一次披上了绿装,争得了长冲岗的第一个“新春气象。”
王大伯把烟锅往桌子上了搕,马上接过话头:“老徐你晓得,这茶场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起来的,是三面红旗的产物,能下马吗?当时洪成领着大家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导,有毛主席撑腰,大家心里亮堂多了,踏实多了,硬是顶住了下马的妖风。”
“今天,你们谁也别争了。”老李已经把火炉、小吊锅端到桌子上来了。
想到这里,我巴不得马上见到老李。“大伯,老李还在这里吗?”
吃过中饭后,老李和王大伯引着我去整个茶场转转、看看。
苍绿苍绿的茶树啊!你是否知道:为了你在这岗上扎根、成长,人民流了多少血汗!经历了多少艰苦曲折的斗争!你是人民用血与汗润育的、灌溉的!
以后,红军在这峰上作过战,流过血;新四军在这峰上作过战,流过血;解放军在这峰上作过战,流过血。
“对!”只见老李,这个在地主、山霸皮鞭下熬过半辈子的长工,“霍”地跳上那磨盘似的巨石,对自己的阶级兄弟激昂地说:“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地下冒出来的,得靠我们用双手去创造。人心齐,泰山移。只要大伙一条心,不愁建设不好。”红旗,把老李的脸映得通红,他那响铮铮的声音,震动着长冲岗,在人们的心坎里久久激荡。寒冬腊月,老李领着大伙到几十里开外的山上割回芭茅、野竹,盖起了茅棚。扯来葛藤,编织箢箕,捡来废铁修打锄头。人们冒着风雪,夜以继日地奋战,把麻骨石一块块挖出来,又从山下挑来一担担土填下去。沉睡了千百年的长冲岗,被搅得日夜不安宁。
场部和职工宿舍就在盘石峰下,清一色的红砖红瓦,被四周的簇簇绿茶映衬着,犹如嵌镶在苍峰间的一颗红灿灿的明珠,又象是屹立在碧海中的一个璀灿晶莹的珊瑚岛。只是在它的旁边,有一小间原来制茶用的茅棚,一看就明白,那是特意为教育青年一代而留下的好教材。
一九三O年“三·二”暴动时,长冲人民举着红旗,拿着锄头、扁担,集结在这盘石峰上,象一股冲决堤坝的滚滚洪流,向地主、山霸家冲去……
王大伯叫王华刚,是这茶场的“开朝元老”,今年六十五岁了。高大的身躯,套着一身宽大的土青布衣裤,挽起的裤腿上沾满了黄泥,肩上扛着一把沙耙,看上去比十年前更年轻、更健旺了。我望着他那结实的身板,说:“大伯,十年不见了,您还象当年一样,那么硬朗。
听到老李的话,她倒有点腼腆了,但马上又放起连珠炮来:“老李,人家一来,你就让他在这劳动。走,老徐,你还没有喝过茶场自产的绿茶吧,可香啦,这回一定要多喝几杯。我先泡茶去啦。”话音刚落,就脚不停地走了。
当时,我们真是一穷二白。秃秃的荒山上,连安身的茅棚也没有一个。记得第一次誓师大会,是在盘石峰上召开的,一面鲜艳的红旗插在一块磨盘似的巨石旁,人们簇拥在四周,老李站在红旗下,一手叉着腰,一手挥舞着:“这山是毛主席领导的军队用生命和鲜血夺回来的,我们能让它再荒下去吗?”
老李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走,我们到屋里去好好聊聊,也快收工了。”
“我们一定要在这里扎下根来,艰苦创业闹革命!”
我看着她那轻捷利索的背影,不觉叹道:辛勤的劳动,艰苦的斗争,换来了长冲岗的一派崭新面貌,也使年轻一代的青春焕发出越来越耀眼的光芒。
这时,我们已经登上了长冲岗的主峰盘石峰。这里的茶长得特别好,叶子特别肥厚,枝芽也特别粗嫩。山顶上两棵常青树也特别青翠。看到这一切,老李十年前给我讲过的事又浮现在眼前:
突然,从坡上传来了一个尖利的声者:“好哇,老徐同志,来了也不到我们家去喝茶,害得我们到处找你。”我抬头一看,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女青年,挑着一担箢箕,一对短辫子在肩上晃动,尖尖的面颊上闪动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我马上认出来,她叫春英,十年前,还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姑娘,体质较单薄,但干什么活都要争着上,不给她任务,就急得要哭。
老李也和大家一起笑着,那笑声是那么豪放、那么舒坦。但马上又略带严肃的神情说:“事情就是这样,什么都要靠斗争,不斗,百事都办不成。”
短短的几句话,拨燃了人们心头的火种:
“难道让这千把亩茶树都干死?”人们焦急地议论着。老李更急。他有空就到东边山上蹲,西边山上转转,摸摸快焦了的茶树,望望远处的山,沉思着。
“啊呀!真想不到你来了,不是听说你调到大学去工作了吗?”王大伯拉住我的手亲切地说:“什么时候到的?”
“嘿嘿,眼下农业大上快上,不勇一点,就要落后啊!”接着,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嘿嘿,我没有做个么事,靠的是青年人的干劲。”王大伯吸着旱烟,轻轻地笑着,兴致勃勃地继续说:“不过,这几年学大寨,打开了我们的眼界,要建好茶场,不能光搞小修小补。不下大决心,彻底治好长冲岗,我们的茶场就不能巩固。”王大伯的话,说得很平常,可是,当我看到眼前山岗上那数千条石岸,那遍布在六十多个山头上的数不清的沟头和一个个坚固结实的石谷坊,算算这一百多双手几年来所搬走的土石方,想一想他们交售给国家的茶叶的重量,我深深地感到:王大伯那几句普普通通的话,凝聚着他们走大寨道路的多大决心,饱含着他们改天换地的多大干劲啊!
我还记得,老李一连两个多月没下山,眼睛熬红了,脸颊消瘦了,头发长得快盖住了耳朵。我开玩笑地说:“老李,歇会儿吧,瞧你那长的头发,都快扎得辫子了。”他不以为然地摸摸自己的脑袋,笑着说:“你不晓得,这才暖和呢!”直到过春节,他才请我这个“理发员”剪了个头。但那几天他还是没有歇,领着我们几个把原来四面通风的茅棚用高粱杆编了道墙,糊上泥巴。老李一面细心地在“墙”上剜着窗口,一面笑着说:“开几个窗子,把春天的阳光迎进来。新春嘛,就得有个新春的气象!
这时,屋子里挤满了人,把我包围起来,这个要我到他家去吃中饭,那个拉我到他家去坐坐,喝杯茶。我不知道回答谁的话好。最后还是王大伯解了围:“唉,徐同志又不只住一两天,以后到你们家去。”
长冲岗啊!在解放你的斗争中,多少人献出了生命,献出了鲜血;在建设你的斗争中,又有多少人流过汗,也曾流过血!血与汗,渗透着你的每一寸土地!
老李,迎着阳光,笑眯眯地指这指那,兴奋地给我谈论着茶场的明天。
职工们正在给茶树翻土,见我们来了,围了拢来,问长问短,格外亲切。只有旁边几个十四、五岁的小姑娘,看了看我,又以探问的眼光互相看了看,其中,一个圆胖脸的小姑娘用手肘碰了碰身旁一个比她高半个头的小伙子,小声地说:“这是谁,你认识吗?”小伙子把嘴一噘:“不认识。”王大伯大声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徐同志,他在的那会儿,你们还在地上爬,吃饭用手抓呢!”说得那几个小姑娘低下头,红了脸。我忍不住笑了笑,说:“是啊,她们在成长,这个茶场也在不断地变化。你看,要再晚几年来,我恐怕要迷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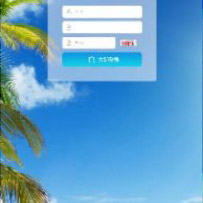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