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寨上望春花
…
高洪见大海不愿离开,俯身揭起一把茅草,指着那些黄中泛绿的小松苗,说:
“我和一个小姑娘搬去的!”
“你们看,这是我们亲手培育的,山脚一线是祖父一代,已经撑天成林了;山腰一线是‘父亲一代,正直插蓝天,现在我们培育的是孙子一代了,看吧,它们也将要成为栋梁之材!”
我们的望春树就要开花了!我们的望春树就要开花了!”
“让我们代你把它栽上吧!”
早饭后,高洪肩扛米袋,手提吊锅和咸菜,来找大海。一见他收拾好的行李担,举起吊锅说:“带上这个就行了,桌凳那里早就备好了!”
上天堂寨那天,大海起得特别早。他打好背包,还特意挑选了一张轻巧的小方桌,两个小方凳。
“如今,老虎洞边的望春树年年开花,花色是粉红的。是什么原因?是洞里的泉水特别?是烈士们用自己的鲜血浇灌了它。”
他们和高洪一起都挺立在天堂寨主峰了,多么象一棵棵擎天的望春树啊。在春天阳光的映照下,那一张张红色的笑脸,正如一朵朵粉红色的望春花,在山顶盛开着。他们顺着高洪手指的方向望去,真的看见了气势壮观的大海了——那不是云海,而是风雷震荡的五洲,云水翻腾的四海!
老虎洞的新主人是一老一少,他们是英山县天堂林场的苗圃培育员。
“快睡吧,快半夜了。青年人不要糟蹋身子!”
平时,高洪对大海很严格。有一天夜里,高洪竟严厉地吼他:
高洪抬起头,看一眼大海,亲呢地说:“这傻孩子,快去穿上大衣,早晨这么冷,小心着凉啊!”
“是啊,住在这洞里挺好呢,喝水都不用挑,有真正的自来水呀!”
高洪,这位在大别山打了二十年游击的老共产党员,一讲起大别山的事,感情是多么激动!他回叙着在老虎洞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大海都听得入迷了。
大海走过去一看,那儿有一块平展的青石板,由三个石墩子支撑着;四周还摆着几块大石头,这就是凳子了。石板石头上长满了青苔。
在哪里培育树苗呢
“我们刚来的时候,你不是说这洞里好象有人住过吗?是的,这洞里确实住过六个人:五个伤员,一个女卫生员。这张石桌子就是那小姑娘和我一道抬进来架好的!”
这棵生长了四十年的望春树,已经有水泥电线杆那么粗了。它高近三丈,树干笔直,枝叶繁茂,四季如伞。每年早春二月,望春树上花蕾丛集,春风一吹,花瓣绽开,香飘十里。到繁春三月,百花争妍,它们便无声无息,渐渐隐去。难怪有人说,这望春花简直可以同腊梅花媲美,风格高尚纯朴。别处的望春花都是雪白的,唯独这老虎洞边的望春花,看上去却略带粉红,更加逗人喜爱。有人说,这可能是与这高山的气候有关,有人却说,这是由于那些栽种它的人的特别浇灌。
是高洪的声音。大海扭头一看,高洪已经攀上寨顶,正望着他们笑呢。于是,大海和他的伙伴一齐奋力向顶峰登攀……
“好啊!象你们这些能文能武的人,还要多培养才够用!”
经过高洪和大海多次分析,都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树苗不适应寨上的气候条件。天堂寨地势高,气温低,俗话说:“四月八,冻死鸭;五月九,冻死牛。”山脚的麦子抽穗了山顶的雪却还没有融化完。再加上山头招风,嫩苗怎经得住!
回到洞里,大海掏出日记本,趴在石桌上,写呀,写呀,写下了革命先烈的传统,写下了自己今后的志愿。
去年早春二月,老虎洞边的望春花盛开着。它以那醉人的芳香,迎来了老虎洞的新主人。
大海听了这席话,笑了。不过高洪看得清,大海的笑有一半是堆在脸上的,不大自然。你看,大海那双手,把信纸折来折去,不知如何是好。
“我这一把土,也加上去吧!”
高洪跑遍了四周的山山岭岭,在一个深谷的岩缝里发现了一棵两尺多高的小望春树。他小心地刨起它来,晚上给伤员们送去了。
天夜里,突然下了一阵大雨,雨点打得瓦片乓乓响,他以为落冰雹了,赶忙从床上爬起来跑到苗圃地里,急得团团转。当他无意地用手托着斗笠遮住一片苗地时,发觉落到自己身上的是雨点,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这山脚、山腰上栽的树,全是他一手培育的苗。去年,党支部决定派林大海给他当助手,正好他在为天堂寨的树苗着急,有时竟急得通宵不眠。大海以为他病了,劝他:“高大爷,我陪着你去看看吧!”高洪以为大海是想着天堂寨的事,对他说:“我已经看过好多次了,栽上的树苗成活的还不到一半!”
高洪正望着大海笑呢:“快进洞去讲吧,怪冷的!”
他这一说,弄得大海有点莫名其妙呢!
“这洞里好象有人住过?”
来了!来了!造林大军由党支部书记扛着一面大旗领着上来了!队伍中,有好多大海的新伙伴、新战友啊!造林大军来到苗圃地里,扯上一把把华山松苗,分成很多小分队,向主峰进军了。高洪领着大海和他的新伙伴,首先绿遍了老虎洞四周,又向顶峰攀去。
他们翻过四道小山梁,来到老虎洞口,衣服上拧得下半斤水来。大海惊异地走进去一看:
“不,是同学来信了。他下乡两年多,贫下中农推荐他上大学了,住在五层楼上呢!”
大别山主峰天堂寨,海拔一千八百七十米,怪石绝壁,攏眼峻峭,气势雄伟。蒸东南面一悬崖脚下有一个老虎洞,长七米,宽五米,成年人可以挺直腰板在里面走动。洞里岩缝中涌出一股清泉,终年不断。老虎润四周,古藤缠绕,杂木环抱,再加上山高烟浓,过去很少有人知道它。就在这老虎洞里,曾经居住过大别山的主人,他们还在洞口边的石头缝里栽种了一棵望春树哩。
“谁能料到呢?”高洪拨弄着燃烧着的枯树枝,又望着大海说,“正当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刘楚达叛变了革命,出卖了我们的同志!那天晚上,天很黑,枪声在老虎洞四周的群山回响。我正要冲上去营救同志,左腿拖不动了,一摸,粘糊糊的,裤子也湿了一片,我受伤了。在嘈杂声中,我听见了那位河北籍小战士高吭的声音:
“你搬去了?”大海不相信。
天亮的时候,天气放晴了。大海从梦中惊醒,一蹬脚,高大爷不在。他赶紧爬起来,穿上衣服,裹紧下乡时父母给他做的那件四斤重的长大衣,掀开洞口的柴草一看,地面上堆着一层冰粒子。透过晨曦,他看见高大爷还在苗圃地里忙碌着。他甩掉棉大衣,跑去了。
那小的才十七岁,是武汉的高中毕业生,去年下乡来到林场的,名叫林大海。他爸爸是海员工人,才起的这个名字。小学毕业时,他爸爸给讲过一次大海日出的壮丽景象,他从此便爱上了大海,吵着要跟爸爸当海员。后来进初中了,报到时,教师问他姓名,他就说:“我姓林,叫大海——很大的大,五湖四海的海!”弄得那位教师也笑了……
高洪往里角指了指:“在那!”
他们在新的宿舍里
“望春树!太好了!”河北籍的小战士接过树苗,惊喜得想立即动手把它裁上。可是,罪恶的子弹打伤了他的两条腿,他没能够站起身来。战友们看到这情景,接过树苗说:
听着高大爷的叙述,大海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他默默地走出洞口,看见望春树显得更加高大,那一朵朵望春花,张开花瓣,象一张张笑脸,正望着他。这时,只有在这时,他才真正感觉到山的亲切,望春花的美,感觉到自己跟这里的一切再也分不开了。他双手抚摸着这高大的望春树,仰望着盛开的望春花,心潮起伏,就象大海的波涛翻滚着,他在树边站了很久,默温着一个伟大的真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高洪一听这语气,心里就象一根针戳了一下,不由得浑身一震。但他马上镇静下来,笑着说:
望春花为啥是粉红色的
“多好的松苗啊,刚出土就受到了这场暴雨和冰雹的袭击,炼出一身铁性来,长大了就不怕风险了!”
高洪一进洞,就被一个年仅十七的河北籍小战士缠住了:“你一定给我们捎来一棵树苗,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亲手装扮大别山!”
大海生着了一堆火,叫高大爷脱下棉裤烘烤着,把长大衣给他披上,要他讲望春花的故事。
“当时我们走进洞口,天色亮了。我抚摸着望春树,仿佛看到大别山上满是松杉。火红的朝霞映照着烈士们殷红的鲜血,大别山也仿佛成了一片红海啊!”
解放后,党和政府在这儿建立了一个林场,打响了向荒山进军的战斗。十几年过去了,山脚的楠竹已为国家献宝,山腰的松杉正在生长成林,唯独主峰一带几次造林,却成活率很低。这对于苗圃培育员高洪来说,心里该有多焦急啊!每天,他只要一看见那光秃秃的寨顶,心里就很不自在:这是老革命根据地的山,怎能叫它荒芜?望见那棵望春树,心里更翻腾得厉害。碰到党支部书记就说:“解放二十多年了,天堂寨还是个和尚头,我们得革它的命呀!”
“不要紧,”高洪显然有些激动了,“那上边不远有宽敝的宿舍,等着我们去住哩!”
“洞里哪有桌凳?”
高洪一听,心头一热,满口应承:“行啊!行啊!给你们挑选一棵长大了能开花的树苗!”
是啊,老根据地的人民,多么希望天堂寨尽快嵌镶在这无限风光的画屏里!
“高大爷,山腰那棵望春树开雪白的花,这棵望春树为什么开粉红色的花呢?”
“象我可不行,进步得这么慢!”
“啊,是家里来信了?老人家都还健旺吧?”
今天,高洪话特别多。他指着大别山林带,高兴地说:
他们住进老虎洞以后,白天在山坡上开荒育树苗,晚上在洞里围着火堆谈天。有时,大海坐在石凳上,趴在石桌上,就着小油灯,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看小说,写日记,新报纸一到,还读给高大爷听呢。这一老一少组成的新家庭,和睦极了。高洪观察着大海的一举一动,有时自个儿也要笑一笑。这笑,从面部表情上只看得出一点点影子来,大海往往觉察不到。高洪是在心里笑啊!
“大海,快上来呀!在天堂寨顶上可以望见更大的海哩!”
“苗子太嫩了,恐怕要冻坏的,得细心照料着才行啊!”
为了这,高洪哪一刻不在每一个细节上寻找着自己的责任?只要苗子一出土,他每天总要去看望三四次,下雨以后,沙泥溅在小树叶片上,他用手摸一摸,要是能够的话,他真想一棵棵给它们洗澡呢。有时,他一个人蹲在地沟里,自言自语:“咳,我的小宝贝,快长吧!”后来,说习惯了,这句口头禅被职工们听去,一传开,都说高洪有一群小孙孙,全在苗圃地里哩!高洪听了人们的议论,心里乐滋滋的,说:“培育树苗,就得象待孩子一样才行啊!”
“那儿离场部五六里,管理不便呀!”大海说。
“等游击队赶到的时候,我们的六位同志全被害了。敌人撤退后,我拖着受伤的左腿,跟着队长来到老虎洞收敛烈士的尸体。在洞里,我亲眼看到,烈士们的鲜血,顺着岩缝,向着望春树,流淌着,流淌着;在洞里,我亲眼看到,烈士们生前摆的沙盘还在这张石桌上。这个沙盘,标志着革命者的理想,她深深地埋在我的心里!”
几个月过去了,斗争环境越来越艰苦。时值严冬,西北风卷裹着鹅毛大雪,把大别山搅得天昏地暗。伤员们在洞里,听到的不是阵阵松涛,而是杂树茅草的哀号;看到的不是充满生机的丛林,而是皑皑白雪覆盖着的荒山。一天晚上,高洪按照计划给伤员们送药草去,伤员们正围着石桌谈笑风生。一看,石桌上摆着整个大别山的沙盘,沙盘上插满了树枝。也许他们在研究解放大别山的战斗吧!其实不是,他们想得更远:伤员们住在这个小小的山洞里,在设计着大别山的未来呀!
过了一会儿,大海又习惯地掏出日记本,提起钢笔,想写几句什么。可是,他又合上日记本,套上钢笔帽,跟高洪道睡了。
老的叫高洪,六十三岁了,是大别山区的老游击队员。咋一听,你会觉得他的名字倒挺文雅呢,一定是个读书人给起的。其实,他压根儿就没个名:高是他的姓,洪是他的辈份。你要是打听这事几,他就会告诉你:“在旧社会,穷人哪里起得了名啊!小时,父母叫我洪儿,后来大了,参加了游击队,大伙就叫我高洪了!
后来,大海想了个主意:培养华山松苗,因为它比油松抗寒力强,高洪同意了。大海又主张在场部附近选块最肥沃的地作苗圃地,认为这样长出的松苗一定更壮些。这一点,高洪却表示反对。他说,那样培育的松苗是表壮里不壮,经不起风雨。他主张到寨顶一带选择苗圃地,还要专选向阳当风的地方。这样,老少二人发生了争论。他们向支部汇报了各自的想法,支部又发动全场职工讨论,大都认为在高寒区培育树苗,从小就经受锻炼,移栽时只挪动一个窝,气候环境适应性要强些。最后,大伙认准了高洪的主张。大海虽还有点不服气,也勉强同意了。经过实地考查,苗圃地就选在老虎洞前那片荒山坡上。
“不能这么看。”高洪亲切地说,“他上大学,你上高山,这同样都是进步啊!我看,你也进步得不慢,回想初进场那阵,住在山腰新盖的宿舍里,不是还不习惯吗?如今在这高寒区扎下了根,住在山洞里,也渐渐习惯了。从山脚到这老虎洞,已经登了一千五百米高了。你进步得快呀,用不了多久,我们还要攀上山顶啦!”
如今,老虎洞前的望春花又盛开了。它正迎接着造林大军的到来。
昔日大别山,是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山脚一带是地主的“座山”,群峰险要处是迷信职业者的“庙山”,天堂寨顶是土匪的“寨山”。他们对于山林,是“秋砍冬烧春不管”,久而久之,这大别山也就成了荒岭杂刺林。
大海深有所悟地,半天没说出话来。他停在开花正旺的望春树边,贪婪地欣赏着望春花。忽然,他象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
那还是一九三二年九月二日,驻在英山的工农红军三面受敌,被迫转移了,临走,把五个伤病员和一个卫生员交给了高洪和另一个游击队员刘楚达。他们连夜把这六个人送到了十分隐蔽的老虎洞。
……
夜很静,战友们用手指头刨土的声音都听得清楚。河北籍小战士呆不住了。他用双肘支撑着身子爬到洞口,抓起一把士来,用颤抖的声音说:
大海呢,两眼紧盯着高大爷:棉裤被雨淋湿了一大截,手脚冻成了紫褐色。再看那五亩多地的华山松苗圃,全盖上了一层茅草。他眼圈红润了,渐渐地,渐渐地,一颗晶莹的泪珠滚落在地上。
新的“宿舍”是什么样儿?
夜里,突然下起雨来,雨点中还夹杂着蚕豆大的冰雹,打在岩石上,象炸豆一般响。猛烈的西北风直往洞里灌。高洪轻手轻脚爬起来,点上小油灯,眯着眼一看温度表,已经零下八度了。大海卷缩在被窝里,睡得正香呢!他把自己的狐皮背褡盖在大海身上,独自穿上蓑衣,戴上斗笠,拿上手电,用柴草堵严洞口,向苗圃地奔去了,嘴里还唠叨着:
其实,高洪的话大海根本没有听清,只觉着耳朵里灌进了声音,扭过头来看一眼高大爷。高洪觉得奇怪,挪过去一看,石桌上放着个信封,大海正拿着一张写满小字的纸出神呢!
这时,太阳已腾起一树高了。群山深谷中,升起一条条乌龙似的烟雾。它们伸长着,春风一吹,搅在一起,到半山腰,就全都舒展葡伏下来。当一切都淹没在云海里的时候,唯独远处的山峰屹立在云海之上,宛如一座座海岛。望春树正在云海边开花,粉红粉红的。大海回想起爸爸曾经讲过的大海日出,如今,他被大别山这壮丽的云海日出迷住了。他尽情欣赏着,惊叹起来:“真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啊!”
望春花迎来了新主人
大海一听,觉得怪新鲜的,一个劲催促:“这就搬行李去!”
望春花在山顶盛开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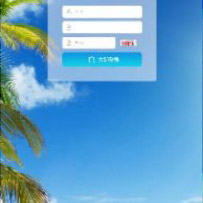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