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河水悠悠
…
太阳不知不觉从山边滑远,把嫣红温柔的光晖洒满青龙山,洒满岩河水。秋水彻里彻外地欢畅,只觉得这山、这水的美景全都是从自己心里溢出来的。
翠芳问:“为么事不穿?
也许有人在涕泪、唏嘘之后,会说我这人太顾及鼻子脸面,死得太冤枉,太不值得了。我要说,这论断未免简单。不错,我没有成为保卫边疆为国捐躯的英雄烈士,甚至连个因公死亡的农民也够不上,没有给母亲带来荣誉的花环、组织的抚恤,然而我一样感到自己死得其所。死,不仅仅是重负的一种瓦解,而是一种蜕变,一种升华,是一个活人对另一个世界的加入,无异于一种新的选择。对死有了这种认识,便不觉得痛苦、恐怖,会视同尘世活人免费去了香港、新加坡,而且不要签证。死是每一个人的归途,王侯将相布衣庶民终究要踏上这条路,不管他是清醒的还是糊涂的,也不管他愿意不愿意。冥冥之中,上帝的手是有召唤能力的,到他面前绝对的公平。毋须悲哀,我不过在归途上动步早一点而已。
秋永虽穷,成绩总是比明平好,所以明平要想得高分,就不能不抄秋水的。秋水拒抄,这一着着实厉害。明平语文、数学分数直线下降,不及格。老师关他的学,不让回去吃饭。
算计来算计去,还差买面、买酒、买烟的钱,约摸三百元。
翠芳一脸红云,窘得直嚷:“你真坏!真坏,到那时还愁不做新的你穿?"
“哎,那个挨铳的也是个糊涂虫,娘心疼死了,气死了。人穷志不能短,人是个脸,树是个皮。莫做亏心事,莫得亏心钱啊!”水子婶又提起了说过无数遍的话。
下平“到那去,也要跟我打个招呼呀?”水子婶心里一团麻。
柴一起砍的,秋水捆的。捆成两大捆,两小捆。小捆是翠芳的,翠芳嫌太少,不中。秋水维持原判,第一次表现了大丈夫气。
订婚很简单,办了两桌酒饭,给翠芳买了一套涤盖棉运动衣。秋水自己盼多年就盼一套运动衫,因为家境困难没有买。订婚的日子给心上人一套自己喜爱的衣服,他想她也一定喜欢。
第二天,还是不见秋水影子,水子婶问明平,明平说“不晓得”,急得她直掉眼泪。
晚饭熟了,秋水还没回来。水子婶倚着们,凉气越来越多地直往心上灌。
这人是不是疯子?
“邱老黑还有打不着的?不过,没打死。是个偷树的,挨了一铳栽了个跟头又跑了,没逮着,搞不清楚是谁。"
走着,走着,秋水说:“歇息一下吧?下边有个岩洞,是我小时和明平抓鱼躲猫猫的地方,想不想看看?”
小卖部。
“是你做的吗?”秋水问。
在一个隐蔽处稍息,明平一看,脸刷地白了:秋水胳膊肉翻了花,淌着浓酽的鲜血,赶紧用毛巾将伤口扎紧。此刻,明平感到自己是个罪人,而那放铳的倒不是罪人。他要背着秋水回家,秋水不让,要自己走。秋水只叫明平把外衣脱给他穿。受伤的胳膊掩住了。
下午四时多,水子婶去小卖部买盐、肥皂。
每天清明节,有一个扛着猎枪的人,跪在那里插祭标,燃纸钱。然后面河而坐,坐为石雕,俨如一尊河神。他的头发全白了,步履蹒跚。只要不死,每个清明节他都会来。这个,连怀疑一切的人也不会怀疑。
老屋的东头就了一面墙,只做了三面墙便添了一间新房。泥砖,里里外外抹上沙泥底子,刷上石灰,亮得晃人,让人清新爽目。秋水别出新裁,安装了自制的“天花板”。天花板没有板,楼枕上钉上自编的篾席,再用米汤糊上报纸,报纸是从废品收购站买来的。花钱不多却很好看,很有点城市房间的味儿。灰尘遮挡了,卫生。冬天暖和,瓦缝的风渗不进来。新房的落成到装饰,除了砌墙是请的师傅干的外,其余的全是秋水自个干的,明平帮了些忙。
秋水慌乱地一笑,一桌好饭好菜好酒还没品出精美的味道来,便不知不觉地晕糊了。刹那时,他莫名其妙地想起把这桌饭菜搬到自个家里去,让母亲看个舒服,吃个痛快。
上山打柴。翠芳拿着冲担也要跟秋水上山。秋水说:
秋水自知失口,一时无言以对。
距秋水结婚的日子——冬月二十日,还有六十天,秋永与母亲在屋里精心里盘算着、忙碌着。
“哪个在偷树?”突如其来,远处传来一声喝问。这声喝问比深山的虎吼更为恐怖。
翠芳守响的时候,翠芳来了。说是来帮帮忙,其实是想见秋水。
“合脚,合脚。”顿时,秋水从脚到头顶麻痒痒的,有一股股微微的电流通过。
水子婶的心也在滚烫地跳。好多年没这样跳过了。在秋水父亲年轻的时侯,才这样跳过。
邻居惠芬嫂主动给水子婶当参谋,说安微的那个老单身邱老黑合适,虽说年纪比水子婶大好大一把,但心肠好,刚直、勤快,打得一手好枪,打到了野味有肉吃,皮子还可以变零用钱。水子婶也听到别的人说过邱老黑的好话,但她还是没答应。她不想再生了。她认定一个死理;再好的男人是冲顺女人来的,未必能巴心巴肝地养育别人的骨肉,象一个母亲那样心疼自己的骨肉。
水开了,等米下锅,水子婶进房打米。一见这情形,赶快退步出来,两个人年轻人还未觉察。
端午节,惠芬回娘家,翠芳关着门和姑姑叨了大半个晚上。惠芬告诉翠芳:“大了,大了罗。姑娘大了,有人打眼不好,没人打眼也不好。将来和谁过日子,是个大事,要靠得实。商店的小蔡、信贷社的小吴,象倒象个干部模样,就是不太点实,难保他们以后不喜新厌旧。我们家是本分人家,依我看还是找个本分人家的儿子好。我婆屋水婶子的秋水,我就很喜欢。莫看他不吃国家饭,可肚子里有墨水,明白得很,心地好,做事踏实,一点不比你说的那两个人差。
待她回来,床上不见人。一看,地下扫得干干净净,缸里的水挑得满满的。揭开锅盖,饭少了,一碗蒸鸡蛋光了。儿子这次吃得不秀气。
翠芳微嗔:“不是我做的,我给你干么事?”
“天黑了,也不晓得回,挖的药呢?"
水子婶以前爱说爱笑,自丈夫去了以后,言笑很少。不过,她不流泪,她把苦水咽进了肚里,化为了骨气,化为了坚韧。天亮开门出工,天黑闭门做饭,喂猪、洗衣、缝补。她相信自己的能力,确把三个儿女拉扯大。她不怕苦,不晓得吃苦是苦。她心里有颗星,这就是儿子秋水!
鄂皖交界处有一条河,叫岩河,源头扎在安徽境内,绵长的身躯却甩在湖北的青峰峡谷之间。岩河水乍一看,绿莹莹的,天的蓝,山的翠恰到好处地溶了进去。细一看,清亮清亮,就是那丈把深的深水潭,也能见到水底的游鱼,爬行的螃蟹,一窜一窜的虾子。水,一年四季凉沁沁的。大旱干涸不了它,小雨也暴涨不了它。它象一个温顺灵丽的山女,沉静地织着自己的春秋,织着自己的妩媚。
“总不能以人命换奖金哪!"
没人的时侯,翠芳叫了秋水一声,“来,秋水!”说着拿出一双崭新的布鞋,黑灯芯绒面,松紧口,鞋底白生生的,一色的白布,一层层叠而成,人称千层底布鞋。秋水明白:其做工只有母亲做的可以媲美,其式样一点不比商店买的塑料底布鞋差。
“吓死胆小的,胀死胆大的,你没看到别人锯了几多哟。干吧!书呆子!这是两省的交界处——混乱地带,山高路险,谁来管,谁管得住?”
岩河长年是温驯的,只有暴雨过后,才昂起头凶暴一阵子。冬日,两侧乃至起伏的地方挂着银光闪闪各式各样的冰凌,别有一种幽美。日日、月月、岁岁,河水不停地流,把年轻人流老了,把年幼的人流大了。岩河流淌的不是水,它是深山丘壑抖出的一轴长卷。
一头猪,不算瘦,有二百多斤,酒宴的肉不用买了,黄豆备了三十斤,酒宴的豆腐已够用。给翠芳备的结婚新衣也差不多,有墨绿色的毛线衣裤,褐红色的风衣,藏青色的西装等等。比起别人家办的虽有些寒酸,好在翠芳不重衣物、钱财,就这么着也将就得过去。
“不、不晓得!”秋水第一次说了不实的话,不由自主地慌乱起来,筷子头拿颠倒了。昏黄的灯光抹淡了脸上的苍白。
作者简介:
蒙蒙亮,两人上路。揣上了秋水妈油煎的面饼,又薄又香,放了很多韭菜、香油。
岩河水的响声听不着了,可那水子婶的唤儿声,相思鸟的啼应声,依稀从门缝里溜进来。
“快跑!快跑!”明平发令。
“合适吗?”翠芳用手摸摸秋水的脚背。
“嗯,娘说的是,得亏心钱就不会得好报。”秋水木木地答着,身上在冒鸡皮疗搭,一股前所未有的虚弱袭来。
秋水紧闭着双目仰卧在那里,围伴他的是虫蚁蚊蝇。头上没有伤痕,脖子上没有绳索,嘴里没有农药味。穿得整整齐齐,用上了他准备结婚的一套涤卡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千层底布鞋,翠芳做的布鞋。
明平颤抖地捧着这封长信,泪珠扑簌簌击打那熟悉的笔迹上,润成大大小小的蓝色晕圈,继而模糊为岩河水一圈连着一圈的涟漪,向着远方荡去。
有一只辫梢的橡皮筋断了,辫子散了一小截。秋水走近:“我给你扎扎吧?”
“吓吓人呗。邱老黑说,他于看山员不是为了拿奖金,是维护森林,维护森林法。
翠芳有心事,不跟外人说,只留与姑姑惠芬说。惠芬的话,翠芳、翠芳的父母都当一回事。惠芬回娘家,翠芳的辫子都是惠芬扎的。
“砰叭——!”一声刺耳的铳响,林间冒出一团硝烟,秋水应声栽倒,天地随之倾斜。
儿子在身边,水子婶温暖了,而且各方面切切实实感到轻松。也许,儿子图的就是这个。
水子婶不哭,那两潭秋水的眼睛,失去了秋水干涸了,再也没有亮闪闪的液体不知是熬干的,还是悄悄放干的。
明乎死命地拖起他就跑。
人群中的一番话,水子婶都听着了,听得心里发紧。一听说山上打了人,头脑嗡嗡乱转,第一个本能的同步反映:我的儿子--秋水--上山的秋水--该不会撞着吧--偷树的--他是挖药的,他不会偷树,他从不做与“偷”字沾边的事。
“我该死——”他狂叫了一声,脚一歪,跌坐在身边的河滩里。
老汉到底是谁,他自己清楚,和他打过交道的人清楚。他,就是安徽老猎手——邱老黑。
“难为你爱上我,我是个寡门子弟,连点彩礼都办不起。"
翠芳没吭声,把又柔又黑的辫子悠悠地甩在他的面前。
于是有了秋水的插秧,有了插秧圆子,有了惠芬家少男少女的见面。
“猫”年寒秋之夜
秋水震惊:“不行!明平哥,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这是犯法的!"
秋水的岩洞边,狗儿刺,爬山虎藤,杜鹃花,芨芨草,马齿苋,几度枯荣。
“是不是到翠芳那去了?”惠芬关切地问。
湾子里抱着孩子晃荡转悠的嫂子们,一到这个时候,一听到这声音,就把孩子撸得紧紧的,走进屋里把门栓上。
“依我说,恋就恋一个好的,恋秋水!将来和我一个湾子过。"
买卖的人凑在一堆叽叽喳喳:“听说没,山上放铳了!"
“好奇,铳打的不是野兔子,是人!”
“傻瓜,明年冬月同床共枕成双对呀!
秋水的两只眼睛又大又亮,黑溜溜,酷象他母亲。秋水之所以叫秋水,就因为眼睛象秋水,还因为他是父母望穿秋水得来的儿子。秋水的名苦是外公想了好久取的。
在我这儿称对象为“亲爱的”还不合俗。不过,我从心底爱你,你真是我“亲爱的”。我只有这最后的一次发言机会了,我再不能左顾右盼连点心里话都不敢写。
也有人说,这人和秋水的死有关,他在这里扬过、忏悔、祈祷、祝福;也有人说,这人和秋水的妈——水子婶有关,在想往日的美事。
他俩溯岩河而上,来到了湖北、安徽交界的青龙山纵深处。人烟寥寥,树不却不少,许多都是一柱冲天的栋梁材。杉本、松木都有。周国有不少新崭崭的树桩,和横七坚八的枝柯,看得出来有人锯过。
“可怕不可怕?不可怕就看。”
明平在秋水上衣口袋发现露出信封的一角。取出一看,信是写给翠芳的,没有封口。众人急切看个明白,没等翠芳完全醒来,信的内容便已展示了--
秋水感谢明平的好意,但没有借他的钱。他想,借钱办喜事,无形中低人一头,说出去,不好听,都是男子汉。再说,借终归是借,迟早要还。他动了挣一笔钱的念头。他决计上山挖药,如果走运,每天挖到几蔸人参、天麻,钱也就够了。不过,这得进深山找寻。
刘耀仑,男,1953年9月生于湖北省英山县英太寨村。毕业于华中师大、鲁迅文学院、北京大学。长期在《长江文艺》编辑部工作,现任小说组长。系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在省内外报刊、电台发表过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评论百余篇,近四十余万字。
岩河水日日夜夜唱着歌吟,赶着不慌不忙的步子。它来自高山之涧,汇密林清泉,忘掉了一路的跌撞摔初曲折回旋,带着通体的澄澈、凉沁,去寻觅从未见过的江海。它的歌吟,快乐的人见出快乐,悲怆的人见出悲怆,逝水在人们眼目中变幻莫测地流动着。
太阳已经落山,离家还有五里路,秋水不走,硬要等到天黑以后再走。
秋水听着,一个个毛孔炸开了。
秋水,读书开窍,一年一个新级别,上了初中上高中。秋水两个姐姐都出嫁了。秋水婶手头没活络钱,全靠养猪、养鸡。只养不吃。猪卖了钱交秋水学费,鸡蛋卖了作油盐润用。秋水婶帮别人干地里活,换工夫请别人做自家的田里活。她要竭尽全力支撑儿子读书。人们都说“秋水是个读书料,将来有出息,会当干部,吃工资饭”。
翠芳:这岩洞真的成了我的洞房。青松藤蔓为帐,绿水清溪奏乐。若是躯体外魂灵果真不灭,我就永远栖居这里。这么大的山,这么长的河,占这么一个不碍眼的洞,大概不会有人愤愤不平。今天,有人会说我是悲剧的主人公,枪手会说我是最好的看山员;将来,人们会公认我是这仙境的主宰者,岩河会多一个故事。
听那声音,明平断定是撞着安徽看山员邱老黑了。此人老光棍,老猎手,枪法极准,兔子、野鸡从他眼前过一枪一个。明平买过他猎卖的野味。
晚霞,顷刻抖落于翠芳的脸上,分外红润娇艳。秋水的鼻翼里扇进了一股少女特有的迷人气息。四只眼睛,对撞出一片片火花,撞得彼比一阵阵颤栗。他象一头沉睡的雄狮突然醒来,猛地将嘴唇贴上了一个女性的嘴唇。巍峨的青山,灿烂的晚霞,清亮的河水,黯然失色,化为乌有。青山的凝重,岩河的温柔,夕阳的神韵,全都填进了两片嘴唇。这是个原始而成熟的奇妙统一。
餐桌上,水子婶问:“水子,山上放铳了,晓得啵?"
水子婶对秋水孤身一人进山不放心,说:“水子,最好邀上明平哥,有个伴。"
从此,明平对秋水安分多了。而且,有旁的孩子欺侮秋水,不用秋水使眼色,明平就会自告奋勇地出拳还击。秋水有的是聪明,明平有的是力气。他俩互通有无,合二为一,成了一对好朋友。秋永烧熟的红薯,明平少不了,明平荷包里偶尔揣上煎熟的河鱼,秋水也能分享。
翠芳不服:“莫小看人,我不是城里豆腐姑娘。”
回应她的是山间的相思鸟的哀鸣;“我儿错掇!我儿错掇!”
秋水把鞋轻轻脱下,拍了拍灰,整整齐齐收放起来。
翠芳两只眸子一转不转,定定地盯着秋永。
明平抢先回答:“到同学家打了一阵子扑克,东西放他那儿了。"
只见她常在傍黑的时候,用四方升子装着茶叶米站在门前,望着波光鳞动的岩河,散扬着茶叶米: “水儿,快回来啊,没吓着啊——快回来,没吓着啊——”
锅里的开水咆咆直跳,盛开一团团雾花。
要想了解到故事个中奥秘,得由作者我远远道来。
在离去的时候,我之所以选在这岩洞,而不是自己的新房,是想让那新房洁白、清净,成后人的礼拜堂。
岩河有岩,沿途不止一个岩洞。靠近青龙山中部的那个岩洞最大,景色幽绝。一到春天,红花、绿叶、青藤、兰香全都拥上了。只因地势险峻,并不是每个山里人都曾光顾。
如所有关心的人都帮找,山上、田里、地里都找过,没见秋水的影子。水子婶连日来没进一粒米,一下子苍老十岁。翠芳两只眼睛变成了两个小红桃。
女孩子一大,俊模样就出来了。十八一枝花,不假。翠芳胸脯上的两砣肉肉还在长,做事、走路有点乱晃动。她用自己攥的钱,买下了一制约肉砣砣的兜兜。戴上兜兜,她是为了让那些青年人不老实的眼睛老实一点。没想到衬衣里影影绰绰的兜兜又添了人们的新奇。
“是你挑柴,还是柴挑你哟?"
高中毕业,秋水完全可以参加高考。可是他死也不参加高考。水子婶把带理的话说了一筐,他就是不考。
翠芳是初中毕业的,书比秋水读得少些,见的世面并不比秋水少,知书识礼的赞誉她一样够得着。翠芳家住在乡镇边上的李家大湾。
先说秋水妈。秋水妈,当地人习惯叫水子婶。她贤惠,父亲是过去的私整先生。她漂亮,人称岩河一枝花。两只眼晴黑溜溜,又大又圆,许多笑意,言语都是那眸子旋出来的,省去了很多嘴上的事。她能干,也能生,三十多岁就生了一串:五个。头四个是女儿,直到第五个是带把儿的,这才刹车。生儿子,在农村是头等大事,全家乐,全垸贺,水子婶很是风光了一阵。
无奈,秋水的腿象灌了铅,想跑跑不动。
“要是结婚没洞房,拿它做洞房才名副其实哩!”秋水打趣地说。
一把锯子,两人轮番地锯。锯铁的锯,用来锯树,艰涩得很。妙就妙在锯的时候一点声音也没有。
夜幕降下,两个黑影向家门靠近。见到母亲,秋水有意地把步子迈得有力。
说是小卖部,并不只卖吃穿用的小百货,它还收购山货、鸡蛋什么的,也是当地轶闻、消息的自动发布站。
翠芳家、舅家、姐姐家、周围同学家都找过了,都没见秋水。
明平,初中毕业未能考上高中,在家务农。很快棒汉子一个,挑驮犁耙,样样拿得起。他已成家。
我决不是因为挨了砰然的一铳离开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契机,一个提醒。我离开得很平静,很坦然,很清醒。我涅槃一般离去。在我遗体上除了那一块灿然的枪花,决再找不到自我绞杀、药杀或他杀的痕迹。务请公安、检察、法医人士不要为我无谓地劳神费力。生前乎平一介草夫,死了何须搞得那么神秘庄严?不要株连他人,更不要追究放铳的人。他的铳放得很准、很及时,而且我认为是完全正当的。他是忠于职守的,称得上是生之世界的勇士,他有成功的胆略。他放的是明枪,不走暗枪,他散言敢做敢当,他是活人的榜样。
不了解底细的人大都冒出此种议论。
寻找的人们嘤嘤的哭泣、放声的哭泣,搅作一团。河水不理会这一切,照样地潺湲作响,鱼儿、虾儿依旧在悠游,在淘气。金黄的阳光泼满了河床,河床两岸的青山,象一片稀释、蜕化了的血。
翠芳,亲爱的翠芳:
六岁,秋水上学,穿的是打补巴的开裆裤,洗得也很干净。和他同坐的明平比他大两岁,开过他好多次玩笑,掀开他的裤子,让他的雀雀亮相。他又气又恼,有一次终于断然采取“报复”措施:不让明平抄写自己的作业!
从此,他变得傻乎乎的,老在自言自语。他再不做茶叶买卖,再也不上青龙山了。他见到别人扛着树筒就发抖,就一通大骂“混帐王八蛋!”
我读了几年书,成绩不算坏。我也做过上大学的梦,想当工程师、当军官、当企业家。可我在寡母身边长大,身上注满了岩河的水,我没有气魄和决心走出这块井底。越大,我越明白善良、纯真戕杀了我自己,折断了自己腾飞的双翼。善良、纯真、聪明、勤劳,在我看来都是灿烂的山花,然而有时经不起风吹雨打,成不了平等竞争、自由进取的通行证。人太清醒了,会有太多的忧烦。活着的时候,我曾奇怪地羡慕傻瓜。
明平主动说借给秋水二百元。明平有钱,春上低价收购茶叶,高价转手外来的贩子,赚了五百多。
这里没有坟茔,有什么值得祭奠?
“不许你这样说。”翠芳用手堵住秋水的嘴巴,“我不是要你买我,是要你娶我,我要你的一颗心。”说罢把头偎进了秋水的胸怀。
"做文象文,做武象武。”惠芬见了秋水总是这么夸。
午餐桌上八碗菜,喷香的腌菜蒸腊肉。绿的豆角炒鲜肉,白的糖拌圆子,还飘着黄蛋花的米酒。端菜的是一个嘴角老挂有笑的姑娘,秋水眼神一抖:象是见过。
“他不放铳?逮一个偷树的,奖他二十元!"
奇怪的是,每年清明节,总有一个老汉前来光顾它。每次来,他都在岩洞口对着岩河燃香焚纸,然后默默地冥坐一整天,直到夕阳泣血方去。这情景是进山打柴的人在岩洞对面见到的。他到底多大年纪,人们估摸不清,只晓得他第一个清明节来时,头发是黑的,第二个清明节,头发泛白了;第三个清明节,满头霜雪。
是,不是。是,不是。猜测复猜测,肯定复否定。可怜天下慈母心。
时隔不久,惠芬叫秋水帮她家插秧,秋永用眼睛对母亲打了个招呼就跟着明平走了。他和明平,同学加伙伴,一对搭档的好手。插秧,两人较着劲比快,手到秧到,鸡啄米似的,水花飞溅。一上午,一天块水田于完了,行成行,距成距,横看竖看都是正经路数。
人们好心给水子婶提亲,再找个男人帮衬帮衬,水子婶咬着嘴唇,摇摇头回绝了。那一阵子,邱老黑几次上门。问:“要不要帮工?”水子婶说:“付不起工钱。”邱老黑说:“不要工钱。”水子婶说:“你这老远来做好事,不敢当。”邱老黑听到这,脸真的黑了。
有一天,惠芬在夸奖的当儿,把秋水打量了好久,看他那端正挺秀的身子条,看他那聪明而不多语的精气神,越看越中意,越看越不收眼,直看得秋水脖子都红起来。
嘻嘻哈哈,笑得抱作一团。
还有五十三天,我苦命的母亲就要成为开怀大笑的婆婆,然而她万万没想到提前给予她的是一场放声大哭。我最敬重、最怜悯的是我母亲。她把我们姐妹们拉扯大很不容易。这辈子你不能做她的儿媳,但愿你真心地做她的女儿,算我多一个妹妹,这是我唯一的遗愿。
明平取出锯子:“来,看上锯子的用途了吧?锯一棵树,抬下去卖,一筒就是几十元,你挖药要挖到猴年马月。"
一家养女百家求。更何况翠芳是李家大垸数得着的人。求亲的不少。有的人虽不明说求爱,却明摆着那个意思。镇上商店的营业员小蔡、信贷社的合同工小吴有事无事往翠芳家跑。翠芳的父母起先还笑脸相迎,援椅、倒茶。后来有一次,小蔡、小吴都在翠芳家撞着了,彼此无端地生起气来,弄得翠芳的父母劝也不是,骂也不是,索性一概不予理睬。即使单个来也免了掇椅端茶的程序。主要是翠芳不喜欢他俩,一见来了,她就去菜园,做些可做可不做的事。
“歇就歇下呗。”水子婶了解儿子,虽是个读书人,里外做事都不懒,不是真累不会歇。
“表哥!”翠芳瞥了一眼,低着头叫了。
路上,秋水发现明平没带挖锄,带的是个小巧的手锯,锯铁用的手锯。“挖药不带挖锄,带手锯干什么?”秋水奇怪。
我离开尘世,自己解脱了,轻松了,她却沉重了。我也许太自私、自爱而不负责了。不过,她长痛不如短痛,忍得一时之痛,比长久地载负着儿子带给她的羞辱要好。我只能以死明心,以死明洁,尽管我不可能与屈子的节举同日而语。我上山错了,一失足成千古恨,错得不可挽回,让母亲心目中的太阳成了没有光华的日蚀。既然不能照亮她心,温暖她心,所以我只有离开她。
“扑通!”翠芳倒在洞口。
谁知福无双至,不久丈夫去外地支援三线建设,被爆破的飞石砸死了。水子婶的悲苦不堪言说,微薄的抚恤金,对于拖儿带女的六口之家犹如杯水车薪。有两个女儿生病相继夭折,还剩下两个女儿和唯一的儿子秋水。
在学校,秋水门门功课得高分。一学期结束,得了几张奖状,贴在家的堂屋正中。水子婶无声地笑了。他没有夸奖儿子,只把儿子揽在怀里极亲热地抚摸着,把他破旧的衣裤抻了抻。抻着抻着,眼里滚出了亮晶晶的东西。
"留有明年冬月穿。”
人们赶到洞口,见到洞里倒下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乖乖,老黑也真黑,对人放铳!”
第二天,秋水没起床,没出门,他告诉母亲:“娘,我累了,我要好好歇一下。"
忽然,一个特殊感应,翠芳想到了岩河翠芳高一脚低一脚径直往河边岩洞走去,一行人跟着她。
果然,很大,象敞开一面墙的房子。翠芳乐得直叫:“哟,象个房子!"
明平一笑:“锯子比锄头能挣钱,跟我走吧!"
别了,翠芳,我是爱你的。你让我生的世界领略了岩河优美动人的一隅。别了,爱我育我的亲人:别了,你这一言难尽的人生!
惠芬笑盈盈地给秋水介绍:“这是我娘家侄姑娘,虽说路隔得远来得少,毕竟来过的。她叫翠芳,比你小两岁哩,这饭菜就是她帮做的。”接着又拍了翠芳的肩膀说过“他叫秋水,依着我们辈行,是你表哥。对了,快叫表哥。他是这里的秀才,叫他不亏。”
"为么事留到明年冬月?"
秋水三岁死了父亲。他记不得父亲,心目中只有母亲。他身上注入了母亲的坚毅、聪慧,比同龄人懂的事多,懂的事早。
“那您的意思——?”翠芳当真了。
“打着了?"
“不可能,不可能的。”明平慌了,眼睛发直:“我去帮你找,我去。”
秋水
“快说,是哪个?不说就放统了!”
整整一天,秋水没回来,水子婶整整一宿不安。
“没见到过卵事,放铳有么事好奇的?”
“不可怕,很大,很亮。不过这地方比较偏僻,没有多少人晓得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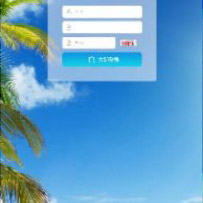
发表评论